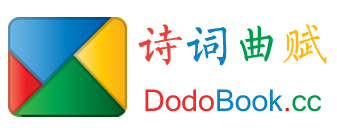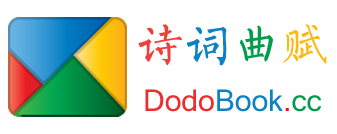家的味道
- 精选散文
- 1535
- 45
- 2015-04-18
身在福中不知福。一样的道理,一刻不离家也就难懂家的温馨了。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的体验更多些:只有那些暂时或永久地放了手的,才让我们觉得出它的珍贵来。
我在这方面的体悟,大约可以从上中学算起。
乡中学离我们村有四五十分钟的脚程。那时,自行车在城里也才是新鲜玩艺儿,出门大多靠一双脚走。乡间没有公路,也没水泥路。多是蜿蜒蛇行在田间地头的尺把来宽的羊肠小道。好一点的大概要算供拖拉机走的机耕路。
没有钟表,但家家户户有广播。要晓得时间全靠听播的是什么节目。广播六点开播。广播前奏一响,母亲就起来为我准备早饭。
学校早上七点半上课,要想不迟到,六点半就应该动身了。六点半,正是开始广播新闻联播的时候。所以这档节目的前奏乐,在我听来,就像田径场上发令员高喊的那一声“预备”一样。
我的早餐都是母亲上灶台炒的炒饭。灶台是土坯垒的,锅是尺八铁锅,烧的一般是稻草。稻草多烟灰,铁锅底易粘结,不消几餐,底上就会结上厚厚的一层,不去除就极耗柴,因而母亲每天起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剔锅底。将铁锅拎至天井里,用一把铁铲,在锅底上细细刮削。于是,锵锵锵的金属刮擦声就刺破了清晨的宁静,也刺破了我的酣梦。
听到锵锵的声音,我就赶忙起身。等刷牙洗脸地收拾好,饭也炒好了。饭里只有酱油,炒好的饭粒油光乌亮,伴着阵阵浓郁的酱香。我通常扒拉几口就吃完了。
细细回味这段日子,觉得家的味道,就是酱香的炒饭味道。
高中是在一个叫作石门湾的小镇上读的。从家里出来,要先走半个钟头,再坐半个钟头的轮船才能到,所以就住校了。半个月回一趟家。
学校有食堂,但米是要自带的。回一次家就带一次米。十六七岁正是能吃的年纪,一次就带毛廿斤。家里出来赶到轮船码头,要走过三个村子,再摆渡到运河对岸去坐船。于是每次乘船,总是父亲用扁担,一头米一头书包地帮我挑到渡口。父亲身材矮小,担着三四十斤的东西,也显得有些佝偻。但走时偏要将一管烟杆咬在嘴里,一边轻飘飘地在我眼前飞,一边不时地将我笼在他的烟里,给我一路的缥缈、亦仙亦幻的感觉。烟闻着有些呛人,但我喜欢。
我们总是非常准点。当父亲把东西拎上渡船的时候,那一班客轮的黑点也在运河的尽头里出现了。于是看我摆过渡去,看我背起书包,扛着米,走进客船的舱内,他才在客轮离岸时的一声长啸里,在南岸渡头的长条石上磕净烟嘴,背身离去。
平日里不在家了,家人便将半月来对我的牵挂,都浓缩在了一个周末里:一二枚发硬了的糕点,一二只皱皮了的果子,或者就是一二颗的糖果吧。但它们在我的眼里,都散发着异样的芳香。因而两周一趟的回家,或者可以更确切地说,是这种异样的芳香,成了我日思夜想的期盼。
后来上了大学,半年才回得一次,这样的感受就更深了。
细细咀嚼这段日子,觉得家的味道,就是呛人的芳香味道。
现在,因为援疆,远行万里,来到了天山脚下。每在一天劳顿之后,敲击键盘,给可爱的小企鹅贴贴“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标签;或者静对电话,默默倾听家人细细絮叨,品味一份缠绵缱绻;再或者听听儿子颇带豪壮的言语,说自己考了多少多少分的时候,真觉得是一种聆听天簌般的享受。
闲时肃立窗前,看大漠日落,遐想日见老去的父母,和那个他们给过我的、如今也在岁月里日渐老去淡去的家,总让我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细细品味如今的日子,家的味道已经说不清道不明了。但有一点却变得愈来愈清晰,那就是,现在离不离家不再重要,那股温暖的味道,我已经总能闻到了。(文/身在沙雅)
我在这方面的体悟,大约可以从上中学算起。
乡中学离我们村有四五十分钟的脚程。那时,自行车在城里也才是新鲜玩艺儿,出门大多靠一双脚走。乡间没有公路,也没水泥路。多是蜿蜒蛇行在田间地头的尺把来宽的羊肠小道。好一点的大概要算供拖拉机走的机耕路。
没有钟表,但家家户户有广播。要晓得时间全靠听播的是什么节目。广播六点开播。广播前奏一响,母亲就起来为我准备早饭。
学校早上七点半上课,要想不迟到,六点半就应该动身了。六点半,正是开始广播新闻联播的时候。所以这档节目的前奏乐,在我听来,就像田径场上发令员高喊的那一声“预备”一样。
我的早餐都是母亲上灶台炒的炒饭。灶台是土坯垒的,锅是尺八铁锅,烧的一般是稻草。稻草多烟灰,铁锅底易粘结,不消几餐,底上就会结上厚厚的一层,不去除就极耗柴,因而母亲每天起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剔锅底。将铁锅拎至天井里,用一把铁铲,在锅底上细细刮削。于是,锵锵锵的金属刮擦声就刺破了清晨的宁静,也刺破了我的酣梦。
听到锵锵的声音,我就赶忙起身。等刷牙洗脸地收拾好,饭也炒好了。饭里只有酱油,炒好的饭粒油光乌亮,伴着阵阵浓郁的酱香。我通常扒拉几口就吃完了。
细细回味这段日子,觉得家的味道,就是酱香的炒饭味道。
高中是在一个叫作石门湾的小镇上读的。从家里出来,要先走半个钟头,再坐半个钟头的轮船才能到,所以就住校了。半个月回一趟家。
学校有食堂,但米是要自带的。回一次家就带一次米。十六七岁正是能吃的年纪,一次就带毛廿斤。家里出来赶到轮船码头,要走过三个村子,再摆渡到运河对岸去坐船。于是每次乘船,总是父亲用扁担,一头米一头书包地帮我挑到渡口。父亲身材矮小,担着三四十斤的东西,也显得有些佝偻。但走时偏要将一管烟杆咬在嘴里,一边轻飘飘地在我眼前飞,一边不时地将我笼在他的烟里,给我一路的缥缈、亦仙亦幻的感觉。烟闻着有些呛人,但我喜欢。
我们总是非常准点。当父亲把东西拎上渡船的时候,那一班客轮的黑点也在运河的尽头里出现了。于是看我摆过渡去,看我背起书包,扛着米,走进客船的舱内,他才在客轮离岸时的一声长啸里,在南岸渡头的长条石上磕净烟嘴,背身离去。
平日里不在家了,家人便将半月来对我的牵挂,都浓缩在了一个周末里:一二枚发硬了的糕点,一二只皱皮了的果子,或者就是一二颗的糖果吧。但它们在我的眼里,都散发着异样的芳香。因而两周一趟的回家,或者可以更确切地说,是这种异样的芳香,成了我日思夜想的期盼。
后来上了大学,半年才回得一次,这样的感受就更深了。
细细咀嚼这段日子,觉得家的味道,就是呛人的芳香味道。
现在,因为援疆,远行万里,来到了天山脚下。每在一天劳顿之后,敲击键盘,给可爱的小企鹅贴贴“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标签;或者静对电话,默默倾听家人细细絮叨,品味一份缠绵缱绻;再或者听听儿子颇带豪壮的言语,说自己考了多少多少分的时候,真觉得是一种聆听天簌般的享受。
闲时肃立窗前,看大漠日落,遐想日见老去的父母,和那个他们给过我的、如今也在岁月里日渐老去淡去的家,总让我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细细品味如今的日子,家的味道已经说不清道不明了。但有一点却变得愈来愈清晰,那就是,现在离不离家不再重要,那股温暖的味道,我已经总能闻到了。(文/身在沙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