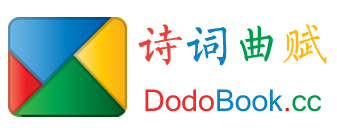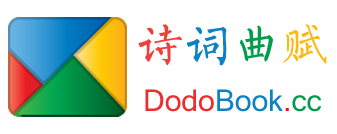赢草岁月
- 精选散文
- 1332
- 28
- 2015-04-18
有时候,真的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一坐,听一听,听着家乡那绿树掩映的地方,远远的传来那熟悉的,遥远的,关于童年的欢乐。哪里,也曾是我们孩提时嬉戏的地方。只是那株散发着清香的洋槐树高了,粗了。那些和我们当初一样的孩童,也把天真在稚气的脸颊肆意的挥洒,那笑脸上,分明也印着关于蓝天的童话,那稚嫩的肩膀,都挑满了幻想,绽放着一颗一颗亮丽的星星。乡音乡情,总是搂了满满一怀,还是拣不完,那么多,那么多。
黄昏时,星期天,那泛着春光的麦田里,我们穿着妈妈做的布鞋,挎着和个头差不多高的担笼,拿着一把铁铲,相约着去挑野菜,打猪草。在麦田里跑啊,跳啊,唱啊的。回想着野菜在妈妈的手中,和雪白的面粉拌在一起,蒸出来的菜疙瘩,那个香啊,梦里都会把小嘴吧唧个不停。想得来劲了,就一边流着涎水,一边把小手里的铁铲挥舞的像舞刀弄剑一般。看到一个大的野菜,就好比拾了一块黄金般的欢欣腾跃。当然,也有心烦意乱的时候,特别是打猪草时,不会选的那么仔细,可是,猪毕竟食欲那么大,需要的草是那么多。身旁的那个担笼啊,总是作对似的总也装不满。于是,趁着伙伴们不注意,就快速的挑一撮麦子垫在底下,心里就一阵“扑腾扑腾”的狂跳,生怕被伙伴们逮着。
累了的时候,我们就会围坐在田埂上,说笑话,讲故事,看一看,比一比,谁挑的多,谁挑的少。这时,就有人提议,我们来玩赢草吧。
“赢草是什么游戏,好玩吗?”有人问。
“那输了怎么办?”有人问。
“我爸爸啊。我爸爸说,他小时候就这么玩的。”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快,一会儿,太阳就翘着尾巴进山了。该回家了,该回到那个有温暖的土炕,有甘甜的白开水的家了。可是,有人哭了,哭了,是因为担笼里的草被赢没了。怎么办,回家要挨打的。
“好办哪,哭什么。我们一起给你挑吧,很快就满了的,但赢了的坚决不能还给你。”
很快的,十几双小手上下翻飞。哭了的笑了,这担笼里的草,比自己原来的要多好多啊,到家里,爸爸说不定还会表扬一番呢。
麦子一天天高了,在夏阳揉动的凉风里,掀起起起伏伏的波浪。在这无边的翠绿鲜活的麦浪中,有一种叫做麦花瓶的草,悄悄地藏匿在麦子中,草茎上,顶着一个一个精巧细致的小瓶子,瓶子颈口,一朵一朵嫩红的小花,和刚刚露出尖的麦穗一起曼舞。它叫麦花瓶,是因为它盛开在麦子杨花的季节。奶奶领着我,小心翼翼的行走在田埂上,一支一支的拔着麦花瓶。我尝过麦花瓶,它那花瓶一般小巧玲珑的果实,吃进嘴里,甜甜的,涩涩的。
“奶奶,麦花瓶那么好吃,为什么要拔呢,把它和麦子碾在一块,吃着一定更香呢。”我仰着头问奶奶。
“怎么不能?怎么不能啊?”
“可是,奶奶你看,我手里已经这么多了,你手里还没有呢。”
“扔了的不算,奶奶,我赢了,我赢了。”
“就是赢了。”我又嘟起嘴。
奶奶学着我的样子,嘟着嘴说:“表扬你还不高兴啊。”
“恐怕是吧,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听你姥姥讲的。”
“故事还不都是瞎编的。”
我又不高兴了,不理奶奶,仔细的拔着麦花瓶。我觉得我的怀里,抱着的,是很多很多美丽好看的仙女。回家的时候,我抱着两大捆麦花瓶,舍不得扔。奶奶说:“扔了吧。”
“就不!我要把它栽在院子里,让它继续开花,还要结出很多种子呢。”
时光匆匆,难忘的赢草岁月,已变成这遥远的回声。但我们那泛绿的田野,还在四季的更替里,变幻着父辈们耕种的辛劳,收获的喜悦。这里,是我永远的赢草岁月,永远的天高云淡。洋槐树下,步履纤陌,我的赢草岁月还在乡音乡情间回旋。偶尔间,我会在田埂上,小路旁,安静的坐着,听顽童嬉闹,看野花怒放。属于我们的这片热土,兴衰日夜,繁华万世。(文/在海角)
黄昏时,星期天,那泛着春光的麦田里,我们穿着妈妈做的布鞋,挎着和个头差不多高的担笼,拿着一把铁铲,相约着去挑野菜,打猪草。在麦田里跑啊,跳啊,唱啊的。回想着野菜在妈妈的手中,和雪白的面粉拌在一起,蒸出来的菜疙瘩,那个香啊,梦里都会把小嘴吧唧个不停。想得来劲了,就一边流着涎水,一边把小手里的铁铲挥舞的像舞刀弄剑一般。看到一个大的野菜,就好比拾了一块黄金般的欢欣腾跃。当然,也有心烦意乱的时候,特别是打猪草时,不会选的那么仔细,可是,猪毕竟食欲那么大,需要的草是那么多。身旁的那个担笼啊,总是作对似的总也装不满。于是,趁着伙伴们不注意,就快速的挑一撮麦子垫在底下,心里就一阵“扑腾扑腾”的狂跳,生怕被伙伴们逮着。
累了的时候,我们就会围坐在田埂上,说笑话,讲故事,看一看,比一比,谁挑的多,谁挑的少。这时,就有人提议,我们来玩赢草吧。
“赢草是什么游戏,好玩吗?”有人问。
“那输了怎么办?”有人问。
“我爸爸啊。我爸爸说,他小时候就这么玩的。”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快,一会儿,太阳就翘着尾巴进山了。该回家了,该回到那个有温暖的土炕,有甘甜的白开水的家了。可是,有人哭了,哭了,是因为担笼里的草被赢没了。怎么办,回家要挨打的。
“好办哪,哭什么。我们一起给你挑吧,很快就满了的,但赢了的坚决不能还给你。”
很快的,十几双小手上下翻飞。哭了的笑了,这担笼里的草,比自己原来的要多好多啊,到家里,爸爸说不定还会表扬一番呢。
麦子一天天高了,在夏阳揉动的凉风里,掀起起起伏伏的波浪。在这无边的翠绿鲜活的麦浪中,有一种叫做麦花瓶的草,悄悄地藏匿在麦子中,草茎上,顶着一个一个精巧细致的小瓶子,瓶子颈口,一朵一朵嫩红的小花,和刚刚露出尖的麦穗一起曼舞。它叫麦花瓶,是因为它盛开在麦子杨花的季节。奶奶领着我,小心翼翼的行走在田埂上,一支一支的拔着麦花瓶。我尝过麦花瓶,它那花瓶一般小巧玲珑的果实,吃进嘴里,甜甜的,涩涩的。
“奶奶,麦花瓶那么好吃,为什么要拔呢,把它和麦子碾在一块,吃着一定更香呢。”我仰着头问奶奶。
“怎么不能?怎么不能啊?”
“可是,奶奶你看,我手里已经这么多了,你手里还没有呢。”
“扔了的不算,奶奶,我赢了,我赢了。”
“就是赢了。”我又嘟起嘴。
奶奶学着我的样子,嘟着嘴说:“表扬你还不高兴啊。”
“恐怕是吧,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听你姥姥讲的。”
“故事还不都是瞎编的。”
我又不高兴了,不理奶奶,仔细的拔着麦花瓶。我觉得我的怀里,抱着的,是很多很多美丽好看的仙女。回家的时候,我抱着两大捆麦花瓶,舍不得扔。奶奶说:“扔了吧。”
“就不!我要把它栽在院子里,让它继续开花,还要结出很多种子呢。”
时光匆匆,难忘的赢草岁月,已变成这遥远的回声。但我们那泛绿的田野,还在四季的更替里,变幻着父辈们耕种的辛劳,收获的喜悦。这里,是我永远的赢草岁月,永远的天高云淡。洋槐树下,步履纤陌,我的赢草岁月还在乡音乡情间回旋。偶尔间,我会在田埂上,小路旁,安静的坐着,听顽童嬉闹,看野花怒放。属于我们的这片热土,兴衰日夜,繁华万世。(文/在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