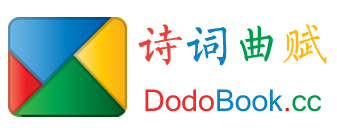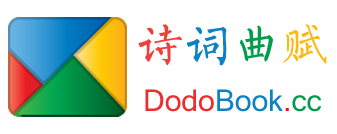彩云之南红土情
- 精选散文
- 1220
- 66
- 2015-04-18
在云南生活了十余年,我把最美的青春时光,留给了这片红土地,身处的是绿色的军营,拥抱的绿色的山水,脚踏的是褐褐的红土地,拥有的广阔的蓝天和白云,而记下的记忆是火红的青春。虽然离开了它,然而它的一抹一彩,一吟一叹,都让我为之挂怀、为之衷情。点点滴滴的回忆,如丝如线如珍如薕,连绵不断余音缠绕,汇成一曲心灵的叹歌。
滇东细雨
今天是西方的圣诞节,在传统的西方此时应多是满天飞雪,山舞银蛇。籍着传统的白胡子圣诞老人分送礼物的期盼,每个儿童,幸福或不幸的,都在心中充满了期许,如棵棵圣诞树上的彩灯,似漫天飞扬的雪花,都在她的心中充盈着无限的幸福和烂漫。
然而同样烂漫的还有彩云之南的冬日雨景。在滇东,由于印度洋湿热气候与大陆冷燥气候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这里一年四季花开不败,绿树长青。尤其在滇东可谓“四季如春”。不过紧接着还有一句话即另一种感受,叫“一雨成冬”。
在今天的圣诞之夜,我们正感受着这成冬的冬雨。它带来了清凉,也带来了清凉中的喜悦,也带来了清凉中的苦恼。
冬雨的天是浑混的。一旦下起来,淅淅漓漓,连日不晴。然而又不是可着劲地下,常常是三五滴漂过,就是微风轻拂,那滴入发丝的清凉,让你真切地体会到刺骨之感。但她又极少予你以落汤鸡的酣畅,极少瓢泼淋漓的苦恼。如少女的轻拂,却又带着忧怨。这轻拂既柔这忧怨也长,常常是三五天不晴。有时即使透些亮光,也很快被浓云所掩,不待她的忧怨发完,不会见阳光重又灿烂。
这浑沌的雨丝,并没有阻断人们生活的脚步。赶摆的,经商的,依旧穿梭往来。卖糍粑的、卖炸土豆的、卖冰糖水的以及各种小东小西的,依然在蒙蒙细雨中开张着,只是在货物上支张伞或支块布,而主人则站在细雨中,顾客也立在细雨中,品尝着,体味着,甚至来上一碗糖冰水,老少咸喜。这时的人们,并不下地,此时耕作季节已过,何况雨中耕作时红土高原上的红粘土如彩色颜料,会染红你的衣服、手脚,极难清洗。好在绿草绿树多,如不耕作,尚不会有太多的麻烦。而城镇中市政建设的发展,也消除了这种泥水飞溅带来的苦恼。
冬雨中的衣着也可谓极尽时尚。只见满街满巷的人依旧脚踏着皮鞋,虽然脚尖上不免有一块块的泥印,并不影响雨中的摩登,因为细雨既不密又不持续,所以地上常常是略湿了又干,略干了又湿。在细雨拂面时的一丝凉意,并没有打击青年人追求时尚的兴头,常常有些女孩仍着短裙,一些男孩仅着单衣。(而我等自北方来此的人,虽居住了较长时间,依然习惯地加上了一层甚至两层毛衣或线衣)。雨中的人们,衣着依然光鲜,笑容依然亮丽,偶然有人打出的花伞就夹杂在这人流中,更多了几分色彩和律动。雨除了给人们的生活增加了另种趣味并未给人们带来不便。所以冬雨也是喜雨。她常来,却不常在。当她去时,阳光依然明媚,花草依然长青,虫鸟依然和鸣。雨后的温度会陡升几度,阳光下依然有灼脸的感觉。爱美的男孩女孩依然会戴上太阳帽,以免把皮肤晒黑晒粗失去光泽。而正有了经常的细雨,这里的树、这里的草、这里的花在冬日里依然保持了光泽。由于温度极少达到0度以下,所以冬雨极少变为冻雨。由于保持一定湿度,所以冬雨会侵至肌骨,因而才会有冬日的体验。(春雨中有的这种体验,主要来自雨与不雨的几度甚至十几度的温差。)
偶而年景也出现过雨夹雪,但通常雪是唱的配角,纷纷扬扬,也煞是多趣,但并不长久,故仍是雨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已是第三天的细雨了,断断续续仍无停的迹象,不知还会再下几天。然而降水却是极其有限,有别于连续的春夏雨就见山洪。门前的南盘江水仍然小溪似地缓流着、潜唱着。
小脚老太
到过云南或听过云南的人,都会知道“云南十八怪”。这是云南的风俗,也是云南的特色,是吸引人的精魂所在,而在“十八怪”中尤有一怪:“小脚老太爬坡比猴子快”。
实际上这说的是云南受大山封闭,在保守的同时也保留了过多的传统,这有香格里拉的自然风情,丽江古城的纳西古乐,傣族歌舞的纯情和优美,还有摩梭族走婚的母系氏族遗风……在这个云集了民族文化的大宝库中,是不包括女子裹小脚的。
记得有位学者曾言:三寸金莲是发明的对中国女人最残酷的刑罚。女子裹脚这种习俗,作为封建糟粕的一种,随着“五四”运动后追求科学民主春风的兴起,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也被投入了旧的历史的火焰之中,至今已近百年。“五四”运动起源地在北京,受其影响较深的北部、东部、中部地区,已鲜见有裹过脚的老太,而在西南一隅的云南,则仍有许多的小脚老太健在,并且在从事着日常的劳作。那句十八怪中的谶语,也正说明了在别处已沉入另一个时代的小脚还有遗存,而且这些见证那个时代苦难的妇女仍然在辛苦地劳作着,继续着和命运的抗争。从另一个方面也映了这里的封闭和落后,也正因此才有了更多的古风遗存。
记得第一次乘火车进入红土高原,那火红的塬顶沟坝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极目搜索着这奇异的红土高原景色。红土地上点缀着绿树红花,煞是光彩,满坡烟叶,行畦错落,在大地上形成织锦。地里有些散落地劳作在田地中的人,有穿汉族衣饰的,也有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劳作中有辛苦也有悠闲,正应了“劳动着快乐着“那句话。突然,透过车窗不远处的田畦中走出了一位个子瘦小的小脚老太,她快步来到路边,是小碎步,麻利地拿起背篓背上肩,沿着小路向铁路边的隧道走来。她的小脚看的很清晰,吸引了许多的旅客屏窗而望。60~70岁的年纪,(由此推断,在1940年代这里仍在延续着裹脚的习俗,至少是贫穷的偏僻的农村),1.5米左右的个子,头上包着头巾,兰黑的粗布袄是斜开襟的,胸前扎着绣有彩边的围裙、明显这围裙在方便劳作的同时也成为日常衣饰装束的一部分。小脚上套着手工的小尖鞋,打着的绑腿更突出了小脚的利索。也许她是即刻想回家为劳作的家人准备饭食?
在云南生活的几年中,经常碰到裹脚的老太。她们大多在60岁以上,从其中比较年轻、动作利落的小脚者看来,她们这地方可能在上世纪的40年代即解放前夕仍存在裹脚现象。这些裹脚的妇女,虽然脚部的畸形发育为她们心灵上带来伤害、肉体上带来痛苦、生活上带来不便,但她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心始终未变。我就曾经见到一位约70岁的小脚太婆每天到外场中队灶上收泔水。低矮的个子,小小双脚的人,却担了两个顶大的泔水桶,每天风雨无阻。也曾见到一位60余岁的小脚太婆手拄一支竹杆,背着一只竹篓,见天出现在营区四周,捡拾垃圾等废弃物。在92年刚到云南时,部队营院至驻地县城有四五公里,那时不象现在有较多的出租车、摩的,那时的交通工具就是小滇马架辕的小马车。我初次到部队报到,也是乘坐的同样的一种小马车,连人带行李就一同送了上来。每逢放假休息,上县城往往也都是坐上小马车,虽则速度慢些,然则悠悠然中也其乐无穷。在赶车的把式中,就曾有一位小脚太婆,我们还经常乘坐她赶的车,非常稳当,而且她还经常是带着个小孙子,带孩子和做生意两不误。车板下的箱中有马吃的草料,也有老少吃的干粮,常常是一跑就是一天,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口自带的水,其中的辛苦可见。然而这样的营运生意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摩的、进而被出租车所取代。从此也就再没见到那位常赶车拉我们上县城的小脚太婆。
云南的少数民族多,全国56个民族中,在云南就有35个。在云南转战的多年生活中,也见过一些山寨中的不少的小脚老太仍然健在。常见她们矮瘦的身影多是围在家中的灶台前,往往背上还用被兜背着小孙儿,在她们不能再出外做事后便担当起了做家什的角色:做饭、养猪、养鸡、带孩子……很少见她们闲下的身影。也许是气候的原因,即使冬日的暖阳下,也极少见到北方街临老人相聚一处晒太阳话家常的情景。
看到她们的身影,也常使我想起十多年前去世的也是裹着小脚的曾外祖母,常常想起她的慈爱、她的善良、她的大度、她的勤劳与坚韧,她的身影常常在梦中出现,她们代表了一个时代。她们从旧时代走来,生活对她们有太多的不公,但她们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追求、对美好的向往。她们更多处在生活的最底层,一生不停地劳作,她们的身上,真正体现了更多的传统中国妇女美德:贤惠、善良、勤劳、积极向上……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们也都逐渐地辞别人世。她们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只留下了一个影子。而影子的背后,却有很多很多东西让人们去思考、去回忆、去探索。看到她们的身影,常让我寄寓无限的关爱、同情、尊敬……以及许许多多说不清的情愫。
兰布背兜
云南有一个奇特景象,几乎每个小孩都是用布背兜背大的。这有别于大巴山的竹背篓、也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摇篮筐、也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抱大孩子的小布兜,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让我从另一个侧面对我生活了十年之久的云南,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云南,更多的迷一样的云南。
背兜是二尺见方的粗布,现也有用绒布的,布面上或绣有各种花木鱼虫,或染有各种人物图案加以装饰。如果挂在墙上,也俨然是一幅精致的装饰品,一贴幅独特的艺术品。布面四角缝有一米多长的带子,用于捆绑。如果是较小的孩子,往往是连脚一起包住,往背上一搭,从肩上至胸前十字交叉,然后捆在腰中,即舒适又挡风,而且干什么活计也不影响,背上的孩子则想睡就睡,不想睡的,两只眼睛东张西望,满足不尽的好奇。这种带孩子的方法,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更方便于生活。同时它也是云南的特有的习俗,在这里很普遍,而别的地方倒极少见到。据一些老人讲,在明清两朝都曾有过大举的移民行动,有些从江西、山西等地迁徙来此地,所以在江西和广东海南等地也曾有这种带孩子的习俗,也许出于同一地域风俗,然后流传各地,而目前唯云南尚保留这种遗风。这种风俗既便于育子,又便于劳作,正合于当时云南作为边陲、经济有待于开发的现实需要,所以不仅得以保留而且倍加珍视。虽然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了,其实用价值亦不占重要地位,但作为风俗仍代代沿习。我的一位战友在上海学习期间,其妻携女带物前往探视,就是用这种背兜背着孩子,一路乘飞机、坐火车,往来甚为方便。
目前有人瞧准商机,做成另一种背兜吊着孩子挂在胸前,孩子四肢可垂可伸。孩子四肢可以活动自由,从而更舒适更人性化,然而这种设计终归让人感觉孩子象在吊着,看着不是很舒服,反不如用背兜背着。即使为了加强对孩子的呵护,用背兜同样可以兜在胸前,包在怀里。这时只是行路尚不碍事,如果要做什么活计就十分不便了。
由于是习俗,习俗对后人便成了习惯,习惯也便成了自然。每次观察,见到无论是行走还是劳作着的父母背上(一般是女同志在背)的孩子都显得十分乖巧,很少见有哭闹的。往往是两只眼睛在你瞧他时他也在瞧着你。有一天,在新华书店选书,发现有位年轻的母亲背着孩子也在选书,母亲拿着书看,走到她背后,只见她背上的小女孩也在双手翻着一本卡通书,书搁在妈妈的脖子上,两只小手在翻,煞有介事的样子。当感到你看她的好奇的目光时,她也向你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当我的儿子出生后,我也曾想着带一块这样的背兜回去,但电话中刚一提及即遭到了妻子的反对,言及在四周有谁用了?怕成了另类。待再次回去时,孩子已大到能下地奔跑了,自然也不好再用,因为此时再用小孩也要坚决反对了。终于未能买一块回去,那怕是作为纪念呢。
现在看到服装店,尤其是各景点的工艺品商店里到处挂有这种作工精巧、绣制华美的小布兜,就有一种购买的欲望。显然,现在其实用性已更多地让位于其工艺性和纪念性了。
彩色沙林
云南有着许许多多的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留下了太多的自然美景:风情万种的西双版纳、曲茎通幽的九乡溶洞、独一无二的石林奇观、秀丽迷人的大理三塔、以及与这美景已完全溶为一体的民俗民风,有燎人心脾的丽江古乐、让人迷离的摩梭走婚……
这些随着近年旅游的兴起,云南的更多的美丽与神奇已逐渐为世人所熟知,然而还有更多的需要人们去认识去发现,其中彩色沙林就是这有待认识的奇景之一。
彩色沙林位于云南曲靖的陆良县。陆良县的沙林同石林县的石林、元谋县的土林并称为云南三大自然岩林奇观而享誉世界,其中尤以石林名气最大,现为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每年前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是几乎每一个到云南旅游物人都必会到的一个景区。相比较而言,土林和沙林则是近几年才为世人所知晓、所重视。彩色沙林几届世界彩色沙雕节的成功举办,迅速为世人瞩目。
彩色沙林位于陆良县城东13公里处,依山傍水于龙海山脉、隐约现于茫茫原始森林之中,得自然之造化、假自然之神功而天成,是为上天遗于云南人民的一块天然奇葩。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投入的加大,相继修建了一些与自然景观溶为一体的建筑、壁画、水库、彩色沙雕,投资修建了高速公路直通入口,培训了导游、增加了商住设施,方便了游客的游玩欣赏,在保持文化气息的同时加大了商业气息,逐渐锻造出一个过硬的旅游品牌。其厚重的历史沧桑感也巩固了这一品牌效应。
据当地县志的地理志记载,考古证据证明,在数十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随着地壳的运动,靠山运动使得青藏高原慢慢隆起,夕日的海底成为了今日的高原丘陵山地,进而孕育了这里的万物众灵。在目前的耕作中,常常能挖到属于那个时代的深海的贝壳和化石。
位于龙海山脚下的彩色沙林,系长期山水冲刷而成今日的大沟壑,土层沙层相貌胶着,而以沙为主,且不同地层所含微量元素不同,成就了不同色彩的沙层,经山洪的不断冲刷,形成了今天形形色色的自然奇观。奇在它不是简单的沟坡,而是成了要个个的沙柱,林立其间,幻化出仙人指路、孙猴翘首、一柱冲天等等形象各异的沙柱造型,一个个相拥相望,蔚蔚然而成为今日的壮观沙林,成为世间一绝;而本为最松散的沙子却能紧固成一体本是一奇,又能成为柱体堪当另一绝;而此沙林则是由各色沙子所构成,主色调为铅红色,间以黄色、兰色、白色、青色,站在极顶上极目望去,如在浮云中,向下俯瞰,沙林柱柱如欲冲天、火红一片,而火红中又不断变幻出不同色调,这是不同色调的大的色块在太阳光下所产生的奇异效果,韵味十足,似要把观者也要拉入林中、溶入景中、混入色中。尤其是在阳光下,就着太阳,彩色的沙子晶光闪亮,幻化流动,给人异样的灵动和感受。
当自然景观赋予文化内涵时,它的吸引力就倍增。彩色沙林据传三国时孟获所居。当年三国鼎立,群豪并起,蜀汉丞相诸葛亮携三顾知遇之恩托孤之重,五出祁山北伐中原,以求统一中国恢复汉室。要逆天而动完成这样的伟业,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是难以成功的。当时的南蛮首领孟获不服蜀汉,屡屡作乱,挑衅蜀汉后方完全。为求得一个稳固的大后方,诸葛亮挑选精兵良将翻山越岭南进蛮疆,深入瘴疫之境,克服酷暑奔波之累、霜毒病疫之险,采纳马谡“攻心为上”之策,出奇计七擒孟获,又以极宽广之胸怀七纵孟获,从而使孟获及其部族心悦诚服的归附蜀汉,稳定了蜀汉的西南后方。据说,孟获的蕃王府就在沙林沟中,而他的族众也就在沙林沟中依山壁凿洞而居。央视大剧《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的外景戏就选在此处拍摄,并修建了孟获王府、孟获军寨和连营。目前这些建筑都予以保留,成为旅游的景观之一,有了历史传说的厚重的文化内涵,单一的景观不再单调,从而成就了今日的4A级景区陆良彩色沙林。
在彩色沙林入口处,有一方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爨龙颜碑”。在20世纪的初叶,在发现的当时就名动大江南北,轰动了考古界和文化界,该碑也被康有为誉为“天下第一奇书”。后又发掘出了“爨子?碑”,称为小爨。碑文字体属于魏碑体,但又带有明显的隶书笔意,显是一种过度书体,对于研究当时书法进步发展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因而陆良也被称为“爨乡”,成为厚重的文化之乡。而大小爨碑立碑林于沙林之侧,更增添了彩色沙林的文化氛围。
而作为沙林近几年文化盛事的是已连续举办了五届国际沙雕节。每年春暖花开的四月,都会有一些世界顶级的沙雕高手云集龙海山下沙林之中,利用天然的各种彩色沙子,演绎出不同的造型,创造出不同的艺术之峰,江成沙雕艺术之林。而彩色沙林的名字,也会随着他们回到世界各地而进一步传扬于世界各地,传扬于世界人民之间。每年的沙雕比赛,已演化为综合的艺术节,汇集了外地与当地的文化精英至此一展才艺。宋祖英、朱军、王小丫、张国立、潘长江、佟铁鑫等大小腕的文化名人也相继在这个舞台上亮相,名人效应更增添了沙林不小的知名度,也为带动经济促进旅游发展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继文化大县、旅游大县,进而建设经济大县,这三大目标正日夜激励着操着浓重土腔的陆良人。(文/雪中飞)
滇东细雨
今天是西方的圣诞节,在传统的西方此时应多是满天飞雪,山舞银蛇。籍着传统的白胡子圣诞老人分送礼物的期盼,每个儿童,幸福或不幸的,都在心中充满了期许,如棵棵圣诞树上的彩灯,似漫天飞扬的雪花,都在她的心中充盈着无限的幸福和烂漫。
然而同样烂漫的还有彩云之南的冬日雨景。在滇东,由于印度洋湿热气候与大陆冷燥气候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这里一年四季花开不败,绿树长青。尤其在滇东可谓“四季如春”。不过紧接着还有一句话即另一种感受,叫“一雨成冬”。
在今天的圣诞之夜,我们正感受着这成冬的冬雨。它带来了清凉,也带来了清凉中的喜悦,也带来了清凉中的苦恼。
冬雨的天是浑混的。一旦下起来,淅淅漓漓,连日不晴。然而又不是可着劲地下,常常是三五滴漂过,就是微风轻拂,那滴入发丝的清凉,让你真切地体会到刺骨之感。但她又极少予你以落汤鸡的酣畅,极少瓢泼淋漓的苦恼。如少女的轻拂,却又带着忧怨。这轻拂既柔这忧怨也长,常常是三五天不晴。有时即使透些亮光,也很快被浓云所掩,不待她的忧怨发完,不会见阳光重又灿烂。
这浑沌的雨丝,并没有阻断人们生活的脚步。赶摆的,经商的,依旧穿梭往来。卖糍粑的、卖炸土豆的、卖冰糖水的以及各种小东小西的,依然在蒙蒙细雨中开张着,只是在货物上支张伞或支块布,而主人则站在细雨中,顾客也立在细雨中,品尝着,体味着,甚至来上一碗糖冰水,老少咸喜。这时的人们,并不下地,此时耕作季节已过,何况雨中耕作时红土高原上的红粘土如彩色颜料,会染红你的衣服、手脚,极难清洗。好在绿草绿树多,如不耕作,尚不会有太多的麻烦。而城镇中市政建设的发展,也消除了这种泥水飞溅带来的苦恼。
冬雨中的衣着也可谓极尽时尚。只见满街满巷的人依旧脚踏着皮鞋,虽然脚尖上不免有一块块的泥印,并不影响雨中的摩登,因为细雨既不密又不持续,所以地上常常是略湿了又干,略干了又湿。在细雨拂面时的一丝凉意,并没有打击青年人追求时尚的兴头,常常有些女孩仍着短裙,一些男孩仅着单衣。(而我等自北方来此的人,虽居住了较长时间,依然习惯地加上了一层甚至两层毛衣或线衣)。雨中的人们,衣着依然光鲜,笑容依然亮丽,偶然有人打出的花伞就夹杂在这人流中,更多了几分色彩和律动。雨除了给人们的生活增加了另种趣味并未给人们带来不便。所以冬雨也是喜雨。她常来,却不常在。当她去时,阳光依然明媚,花草依然长青,虫鸟依然和鸣。雨后的温度会陡升几度,阳光下依然有灼脸的感觉。爱美的男孩女孩依然会戴上太阳帽,以免把皮肤晒黑晒粗失去光泽。而正有了经常的细雨,这里的树、这里的草、这里的花在冬日里依然保持了光泽。由于温度极少达到0度以下,所以冬雨极少变为冻雨。由于保持一定湿度,所以冬雨会侵至肌骨,因而才会有冬日的体验。(春雨中有的这种体验,主要来自雨与不雨的几度甚至十几度的温差。)
偶而年景也出现过雨夹雪,但通常雪是唱的配角,纷纷扬扬,也煞是多趣,但并不长久,故仍是雨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已是第三天的细雨了,断断续续仍无停的迹象,不知还会再下几天。然而降水却是极其有限,有别于连续的春夏雨就见山洪。门前的南盘江水仍然小溪似地缓流着、潜唱着。
小脚老太
到过云南或听过云南的人,都会知道“云南十八怪”。这是云南的风俗,也是云南的特色,是吸引人的精魂所在,而在“十八怪”中尤有一怪:“小脚老太爬坡比猴子快”。
实际上这说的是云南受大山封闭,在保守的同时也保留了过多的传统,这有香格里拉的自然风情,丽江古城的纳西古乐,傣族歌舞的纯情和优美,还有摩梭族走婚的母系氏族遗风……在这个云集了民族文化的大宝库中,是不包括女子裹小脚的。
记得有位学者曾言:三寸金莲是发明的对中国女人最残酷的刑罚。女子裹脚这种习俗,作为封建糟粕的一种,随着“五四”运动后追求科学民主春风的兴起,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也被投入了旧的历史的火焰之中,至今已近百年。“五四”运动起源地在北京,受其影响较深的北部、东部、中部地区,已鲜见有裹过脚的老太,而在西南一隅的云南,则仍有许多的小脚老太健在,并且在从事着日常的劳作。那句十八怪中的谶语,也正说明了在别处已沉入另一个时代的小脚还有遗存,而且这些见证那个时代苦难的妇女仍然在辛苦地劳作着,继续着和命运的抗争。从另一个方面也映了这里的封闭和落后,也正因此才有了更多的古风遗存。
记得第一次乘火车进入红土高原,那火红的塬顶沟坝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极目搜索着这奇异的红土高原景色。红土地上点缀着绿树红花,煞是光彩,满坡烟叶,行畦错落,在大地上形成织锦。地里有些散落地劳作在田地中的人,有穿汉族衣饰的,也有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劳作中有辛苦也有悠闲,正应了“劳动着快乐着“那句话。突然,透过车窗不远处的田畦中走出了一位个子瘦小的小脚老太,她快步来到路边,是小碎步,麻利地拿起背篓背上肩,沿着小路向铁路边的隧道走来。她的小脚看的很清晰,吸引了许多的旅客屏窗而望。60~70岁的年纪,(由此推断,在1940年代这里仍在延续着裹脚的习俗,至少是贫穷的偏僻的农村),1.5米左右的个子,头上包着头巾,兰黑的粗布袄是斜开襟的,胸前扎着绣有彩边的围裙、明显这围裙在方便劳作的同时也成为日常衣饰装束的一部分。小脚上套着手工的小尖鞋,打着的绑腿更突出了小脚的利索。也许她是即刻想回家为劳作的家人准备饭食?
在云南生活的几年中,经常碰到裹脚的老太。她们大多在60岁以上,从其中比较年轻、动作利落的小脚者看来,她们这地方可能在上世纪的40年代即解放前夕仍存在裹脚现象。这些裹脚的妇女,虽然脚部的畸形发育为她们心灵上带来伤害、肉体上带来痛苦、生活上带来不便,但她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心始终未变。我就曾经见到一位约70岁的小脚太婆每天到外场中队灶上收泔水。低矮的个子,小小双脚的人,却担了两个顶大的泔水桶,每天风雨无阻。也曾见到一位60余岁的小脚太婆手拄一支竹杆,背着一只竹篓,见天出现在营区四周,捡拾垃圾等废弃物。在92年刚到云南时,部队营院至驻地县城有四五公里,那时不象现在有较多的出租车、摩的,那时的交通工具就是小滇马架辕的小马车。我初次到部队报到,也是乘坐的同样的一种小马车,连人带行李就一同送了上来。每逢放假休息,上县城往往也都是坐上小马车,虽则速度慢些,然则悠悠然中也其乐无穷。在赶车的把式中,就曾有一位小脚太婆,我们还经常乘坐她赶的车,非常稳当,而且她还经常是带着个小孙子,带孩子和做生意两不误。车板下的箱中有马吃的草料,也有老少吃的干粮,常常是一跑就是一天,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口自带的水,其中的辛苦可见。然而这样的营运生意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摩的、进而被出租车所取代。从此也就再没见到那位常赶车拉我们上县城的小脚太婆。
云南的少数民族多,全国56个民族中,在云南就有35个。在云南转战的多年生活中,也见过一些山寨中的不少的小脚老太仍然健在。常见她们矮瘦的身影多是围在家中的灶台前,往往背上还用被兜背着小孙儿,在她们不能再出外做事后便担当起了做家什的角色:做饭、养猪、养鸡、带孩子……很少见她们闲下的身影。也许是气候的原因,即使冬日的暖阳下,也极少见到北方街临老人相聚一处晒太阳话家常的情景。
看到她们的身影,也常使我想起十多年前去世的也是裹着小脚的曾外祖母,常常想起她的慈爱、她的善良、她的大度、她的勤劳与坚韧,她的身影常常在梦中出现,她们代表了一个时代。她们从旧时代走来,生活对她们有太多的不公,但她们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追求、对美好的向往。她们更多处在生活的最底层,一生不停地劳作,她们的身上,真正体现了更多的传统中国妇女美德:贤惠、善良、勤劳、积极向上……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们也都逐渐地辞别人世。她们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只留下了一个影子。而影子的背后,却有很多很多东西让人们去思考、去回忆、去探索。看到她们的身影,常让我寄寓无限的关爱、同情、尊敬……以及许许多多说不清的情愫。
兰布背兜
云南有一个奇特景象,几乎每个小孩都是用布背兜背大的。这有别于大巴山的竹背篓、也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摇篮筐、也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抱大孩子的小布兜,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让我从另一个侧面对我生活了十年之久的云南,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云南,更多的迷一样的云南。
背兜是二尺见方的粗布,现也有用绒布的,布面上或绣有各种花木鱼虫,或染有各种人物图案加以装饰。如果挂在墙上,也俨然是一幅精致的装饰品,一贴幅独特的艺术品。布面四角缝有一米多长的带子,用于捆绑。如果是较小的孩子,往往是连脚一起包住,往背上一搭,从肩上至胸前十字交叉,然后捆在腰中,即舒适又挡风,而且干什么活计也不影响,背上的孩子则想睡就睡,不想睡的,两只眼睛东张西望,满足不尽的好奇。这种带孩子的方法,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更方便于生活。同时它也是云南的特有的习俗,在这里很普遍,而别的地方倒极少见到。据一些老人讲,在明清两朝都曾有过大举的移民行动,有些从江西、山西等地迁徙来此地,所以在江西和广东海南等地也曾有这种带孩子的习俗,也许出于同一地域风俗,然后流传各地,而目前唯云南尚保留这种遗风。这种风俗既便于育子,又便于劳作,正合于当时云南作为边陲、经济有待于开发的现实需要,所以不仅得以保留而且倍加珍视。虽然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了,其实用价值亦不占重要地位,但作为风俗仍代代沿习。我的一位战友在上海学习期间,其妻携女带物前往探视,就是用这种背兜背着孩子,一路乘飞机、坐火车,往来甚为方便。
目前有人瞧准商机,做成另一种背兜吊着孩子挂在胸前,孩子四肢可垂可伸。孩子四肢可以活动自由,从而更舒适更人性化,然而这种设计终归让人感觉孩子象在吊着,看着不是很舒服,反不如用背兜背着。即使为了加强对孩子的呵护,用背兜同样可以兜在胸前,包在怀里。这时只是行路尚不碍事,如果要做什么活计就十分不便了。
由于是习俗,习俗对后人便成了习惯,习惯也便成了自然。每次观察,见到无论是行走还是劳作着的父母背上(一般是女同志在背)的孩子都显得十分乖巧,很少见有哭闹的。往往是两只眼睛在你瞧他时他也在瞧着你。有一天,在新华书店选书,发现有位年轻的母亲背着孩子也在选书,母亲拿着书看,走到她背后,只见她背上的小女孩也在双手翻着一本卡通书,书搁在妈妈的脖子上,两只小手在翻,煞有介事的样子。当感到你看她的好奇的目光时,她也向你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当我的儿子出生后,我也曾想着带一块这样的背兜回去,但电话中刚一提及即遭到了妻子的反对,言及在四周有谁用了?怕成了另类。待再次回去时,孩子已大到能下地奔跑了,自然也不好再用,因为此时再用小孩也要坚决反对了。终于未能买一块回去,那怕是作为纪念呢。
现在看到服装店,尤其是各景点的工艺品商店里到处挂有这种作工精巧、绣制华美的小布兜,就有一种购买的欲望。显然,现在其实用性已更多地让位于其工艺性和纪念性了。
彩色沙林
云南有着许许多多的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留下了太多的自然美景:风情万种的西双版纳、曲茎通幽的九乡溶洞、独一无二的石林奇观、秀丽迷人的大理三塔、以及与这美景已完全溶为一体的民俗民风,有燎人心脾的丽江古乐、让人迷离的摩梭走婚……
这些随着近年旅游的兴起,云南的更多的美丽与神奇已逐渐为世人所熟知,然而还有更多的需要人们去认识去发现,其中彩色沙林就是这有待认识的奇景之一。
彩色沙林位于云南曲靖的陆良县。陆良县的沙林同石林县的石林、元谋县的土林并称为云南三大自然岩林奇观而享誉世界,其中尤以石林名气最大,现为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每年前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是几乎每一个到云南旅游物人都必会到的一个景区。相比较而言,土林和沙林则是近几年才为世人所知晓、所重视。彩色沙林几届世界彩色沙雕节的成功举办,迅速为世人瞩目。
彩色沙林位于陆良县城东13公里处,依山傍水于龙海山脉、隐约现于茫茫原始森林之中,得自然之造化、假自然之神功而天成,是为上天遗于云南人民的一块天然奇葩。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投入的加大,相继修建了一些与自然景观溶为一体的建筑、壁画、水库、彩色沙雕,投资修建了高速公路直通入口,培训了导游、增加了商住设施,方便了游客的游玩欣赏,在保持文化气息的同时加大了商业气息,逐渐锻造出一个过硬的旅游品牌。其厚重的历史沧桑感也巩固了这一品牌效应。
据当地县志的地理志记载,考古证据证明,在数十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随着地壳的运动,靠山运动使得青藏高原慢慢隆起,夕日的海底成为了今日的高原丘陵山地,进而孕育了这里的万物众灵。在目前的耕作中,常常能挖到属于那个时代的深海的贝壳和化石。
位于龙海山脚下的彩色沙林,系长期山水冲刷而成今日的大沟壑,土层沙层相貌胶着,而以沙为主,且不同地层所含微量元素不同,成就了不同色彩的沙层,经山洪的不断冲刷,形成了今天形形色色的自然奇观。奇在它不是简单的沟坡,而是成了要个个的沙柱,林立其间,幻化出仙人指路、孙猴翘首、一柱冲天等等形象各异的沙柱造型,一个个相拥相望,蔚蔚然而成为今日的壮观沙林,成为世间一绝;而本为最松散的沙子却能紧固成一体本是一奇,又能成为柱体堪当另一绝;而此沙林则是由各色沙子所构成,主色调为铅红色,间以黄色、兰色、白色、青色,站在极顶上极目望去,如在浮云中,向下俯瞰,沙林柱柱如欲冲天、火红一片,而火红中又不断变幻出不同色调,这是不同色调的大的色块在太阳光下所产生的奇异效果,韵味十足,似要把观者也要拉入林中、溶入景中、混入色中。尤其是在阳光下,就着太阳,彩色的沙子晶光闪亮,幻化流动,给人异样的灵动和感受。
当自然景观赋予文化内涵时,它的吸引力就倍增。彩色沙林据传三国时孟获所居。当年三国鼎立,群豪并起,蜀汉丞相诸葛亮携三顾知遇之恩托孤之重,五出祁山北伐中原,以求统一中国恢复汉室。要逆天而动完成这样的伟业,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是难以成功的。当时的南蛮首领孟获不服蜀汉,屡屡作乱,挑衅蜀汉后方完全。为求得一个稳固的大后方,诸葛亮挑选精兵良将翻山越岭南进蛮疆,深入瘴疫之境,克服酷暑奔波之累、霜毒病疫之险,采纳马谡“攻心为上”之策,出奇计七擒孟获,又以极宽广之胸怀七纵孟获,从而使孟获及其部族心悦诚服的归附蜀汉,稳定了蜀汉的西南后方。据说,孟获的蕃王府就在沙林沟中,而他的族众也就在沙林沟中依山壁凿洞而居。央视大剧《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的外景戏就选在此处拍摄,并修建了孟获王府、孟获军寨和连营。目前这些建筑都予以保留,成为旅游的景观之一,有了历史传说的厚重的文化内涵,单一的景观不再单调,从而成就了今日的4A级景区陆良彩色沙林。
在彩色沙林入口处,有一方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爨龙颜碑”。在20世纪的初叶,在发现的当时就名动大江南北,轰动了考古界和文化界,该碑也被康有为誉为“天下第一奇书”。后又发掘出了“爨子?碑”,称为小爨。碑文字体属于魏碑体,但又带有明显的隶书笔意,显是一种过度书体,对于研究当时书法进步发展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因而陆良也被称为“爨乡”,成为厚重的文化之乡。而大小爨碑立碑林于沙林之侧,更增添了彩色沙林的文化氛围。
而作为沙林近几年文化盛事的是已连续举办了五届国际沙雕节。每年春暖花开的四月,都会有一些世界顶级的沙雕高手云集龙海山下沙林之中,利用天然的各种彩色沙子,演绎出不同的造型,创造出不同的艺术之峰,江成沙雕艺术之林。而彩色沙林的名字,也会随着他们回到世界各地而进一步传扬于世界各地,传扬于世界人民之间。每年的沙雕比赛,已演化为综合的艺术节,汇集了外地与当地的文化精英至此一展才艺。宋祖英、朱军、王小丫、张国立、潘长江、佟铁鑫等大小腕的文化名人也相继在这个舞台上亮相,名人效应更增添了沙林不小的知名度,也为带动经济促进旅游发展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继文化大县、旅游大县,进而建设经济大县,这三大目标正日夜激励着操着浓重土腔的陆良人。(文/雪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