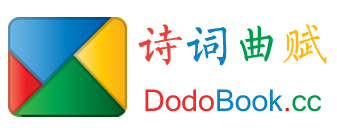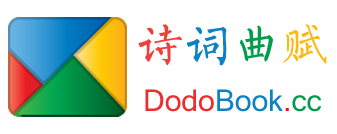我和母亲的约定
- 精选散文
- 645
- 84
- 2015-04-18
明天,农历二月初十,父亲的祭日。
俗话说,养儿防老,就在病榻上那几天。可父亲一点尽孝的机会都不曾给过我们。
那一年的二月初十,也是阳光明媚。刚上完一天课,泡了一杯茶,在教师宿舍的阳台上看书。二叔匆匆忙忙赶来,两条裤腿挽得一高一低,腿上还带着没来得及搓洗的泥土,老远就朝着宿舍叫我的名字。近了,神色凝重,哽咽了好一阵子,才说出:“你爸爸死了”。
“我爸爸死了,我爸爸死了,我爸爸怎么就死了?周末我才跟妻子,二哥、二嫂回老家,帮家里点玉米、打底肥,父亲怕挑粪弄脏我们衣服,一个人挑这淋完了亩多地。怎么我爸爸就死了?”我蒙了半响。
父亲是在犁田的时候,坐在新翻的田埂上死的,一只手扶着犁头炳,另一只手里捏着赶牛鞭。我家那头老黄牛就呆呆地站在田埂上,似乎等待父亲醒过来。母亲带着两岁的侄女,就在旁边的干田里割牛草。当母亲发现老黄牛呆呆站着不动,匆匆赶过去时,父亲已然完成了他生命定型。
太突然了,父亲走得太突然!刚刚把我们几姊妹养大,开始工作,还没等到我们孝敬他老人家;也没等到近在咫尺的相濡以沫的母亲说一句话,甚至连一支纸烟都没来得及抽,就这样毫无征兆地走了!
几姊妹一边伤心流泪,一边给父亲料理后事。买棺材,扯孝布,给父亲缝制寿衣,整日里昏天暗地。因为要安慰母亲,又觉得愧对父亲几十年的养育,一直等到过了头七才回学校上班。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可也读过近十年私塾。以往村子里的老人们过世,都是父亲代家人给老人作祭文。还在出殡时声情并茂念读。可父亲去世时,兄妹几个都悲痛欲绝,村子里又没了能作祭文的人,这一仪式就省略了。这更加重了我的负罪感。
以后每次回老家,看着父亲喂养的老黄牛,不免要问问,看着挂在墙锈蚀的犁头,不禁要摸摸,看着堆在角落的油黄的锄柄,总会情不自禁要闻一闻。庄家地旁边的大石头上,总有父亲歇气抽旱烟的幻影,樱桃坡的丛林里,老是传来锄头磕碰石头的声音。父亲舀纸时的山歌,织席时的口哨也总在耳边萦绕。
这些感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就此写了一首散文诗。寄到一家杂志社,居然发表了。
从来没有上过学堂的母亲,听说我为父亲写了一篇文章,硬要我当面读给她听。我哽咽的读着,母亲伤心的听,听完后,她居然满足的笑了。对我说:你爸这辈子总算没白活,喂了你们几个,尽管没得到享受,却得到这么好一篇祭文。
是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这样那样,这会勤劳辛苦,那会游手好闲,总要等到出末了的祭文,那才是真正盖棺定论。
老家的人都在乎这个,母亲也在乎。
母亲为父亲感到宽慰,也流露出一丝羡慕。我告诉她:“妈,以后,我也给你老写一篇。”母亲高兴地眼泪都流出来了。说:“我等到你读给我听了,我就把眼睛闭上。”我们娘俩相视一笑。
转眼十七年过去了,这十七年里,我和妻子成家了,孩子都十四岁了。我们从当初任教的乡村调到镇上,从镇上辗转到城里。
母亲也随着我们一同转辗转。给我们带孩子,做饭,种菜。一家人其乐融融。
就在父亲走后不久,母亲担心我们到时忙天赶地,托老家的邻居们做好了棺材。后来又招裁缝缝制了几套寿衣。前些时候连上山时,后人们披的麻,戴的孝也买来压在箱底。每次我们劝她,她总说:“我把什么准备好,免得以后你们麻烦。”然后望着我,要说什么。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便打断她的话:“最近工作很忙。”
明天,又是二月初十,晚饭时,又得给父亲敬饭,敬饭时,母亲又得对父亲说:“老头子,你没福气,我比你多享了十七年的福,等孩子读给我听了,我就来陪你。”
母亲!你能理解我的“最近工作很忙”?(文/huangliwei)
俗话说,养儿防老,就在病榻上那几天。可父亲一点尽孝的机会都不曾给过我们。
那一年的二月初十,也是阳光明媚。刚上完一天课,泡了一杯茶,在教师宿舍的阳台上看书。二叔匆匆忙忙赶来,两条裤腿挽得一高一低,腿上还带着没来得及搓洗的泥土,老远就朝着宿舍叫我的名字。近了,神色凝重,哽咽了好一阵子,才说出:“你爸爸死了”。
“我爸爸死了,我爸爸死了,我爸爸怎么就死了?周末我才跟妻子,二哥、二嫂回老家,帮家里点玉米、打底肥,父亲怕挑粪弄脏我们衣服,一个人挑这淋完了亩多地。怎么我爸爸就死了?”我蒙了半响。
父亲是在犁田的时候,坐在新翻的田埂上死的,一只手扶着犁头炳,另一只手里捏着赶牛鞭。我家那头老黄牛就呆呆地站在田埂上,似乎等待父亲醒过来。母亲带着两岁的侄女,就在旁边的干田里割牛草。当母亲发现老黄牛呆呆站着不动,匆匆赶过去时,父亲已然完成了他生命定型。
太突然了,父亲走得太突然!刚刚把我们几姊妹养大,开始工作,还没等到我们孝敬他老人家;也没等到近在咫尺的相濡以沫的母亲说一句话,甚至连一支纸烟都没来得及抽,就这样毫无征兆地走了!
几姊妹一边伤心流泪,一边给父亲料理后事。买棺材,扯孝布,给父亲缝制寿衣,整日里昏天暗地。因为要安慰母亲,又觉得愧对父亲几十年的养育,一直等到过了头七才回学校上班。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可也读过近十年私塾。以往村子里的老人们过世,都是父亲代家人给老人作祭文。还在出殡时声情并茂念读。可父亲去世时,兄妹几个都悲痛欲绝,村子里又没了能作祭文的人,这一仪式就省略了。这更加重了我的负罪感。
以后每次回老家,看着父亲喂养的老黄牛,不免要问问,看着挂在墙锈蚀的犁头,不禁要摸摸,看着堆在角落的油黄的锄柄,总会情不自禁要闻一闻。庄家地旁边的大石头上,总有父亲歇气抽旱烟的幻影,樱桃坡的丛林里,老是传来锄头磕碰石头的声音。父亲舀纸时的山歌,织席时的口哨也总在耳边萦绕。
这些感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就此写了一首散文诗。寄到一家杂志社,居然发表了。
从来没有上过学堂的母亲,听说我为父亲写了一篇文章,硬要我当面读给她听。我哽咽的读着,母亲伤心的听,听完后,她居然满足的笑了。对我说:你爸这辈子总算没白活,喂了你们几个,尽管没得到享受,却得到这么好一篇祭文。
是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这样那样,这会勤劳辛苦,那会游手好闲,总要等到出末了的祭文,那才是真正盖棺定论。
老家的人都在乎这个,母亲也在乎。
母亲为父亲感到宽慰,也流露出一丝羡慕。我告诉她:“妈,以后,我也给你老写一篇。”母亲高兴地眼泪都流出来了。说:“我等到你读给我听了,我就把眼睛闭上。”我们娘俩相视一笑。
转眼十七年过去了,这十七年里,我和妻子成家了,孩子都十四岁了。我们从当初任教的乡村调到镇上,从镇上辗转到城里。
母亲也随着我们一同转辗转。给我们带孩子,做饭,种菜。一家人其乐融融。
就在父亲走后不久,母亲担心我们到时忙天赶地,托老家的邻居们做好了棺材。后来又招裁缝缝制了几套寿衣。前些时候连上山时,后人们披的麻,戴的孝也买来压在箱底。每次我们劝她,她总说:“我把什么准备好,免得以后你们麻烦。”然后望着我,要说什么。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便打断她的话:“最近工作很忙。”
明天,又是二月初十,晚饭时,又得给父亲敬饭,敬饭时,母亲又得对父亲说:“老头子,你没福气,我比你多享了十七年的福,等孩子读给我听了,我就来陪你。”
母亲!你能理解我的“最近工作很忙”?(文/huangli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