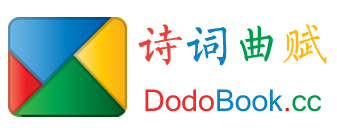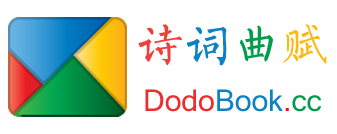夫家祖宅的断壁残垣
- 精选散文
- 584
- 12
- 2015-04-18
孩子的二爷从新疆回来探家,跟我84岁高龄的公公去老家看塌了大半拉的百年祖宅。早些年间公公把房子借给村里的一个族弟住,老人的妻子死于产后风,拉扯大遗留下来的唯一血脉,该子成亲时,老人把原住房腾给儿子,自己就住在村里的牲口栏里。我公公的另一个族兄看其可怜,就商量我家老爷子让他住在我们老家闲置的这幢老宅。
三十五年前,老宅还算齐整,远不像此际这般破败不堪,那时公公去世没几天的母亲是一个很要好很洁净的老婆婆,她的住屋可是井井有条。尽管房顶是麦草苫的,炕及灶台是泥巴抹的,房间也很狭小,但满是残留的温馨的烟火味儿。那时见证着曾经的盎然生机的三个大燕窝还完好的挂在屋檐下。外墙上肥肥的壁虎急急爬行的样子有几分滑稽,墙缝里的壁虎蛋很多;墙顶上的几株狗尾巴草哦满潇洒地在风中摇摆,不断的弯腰挑衅婆婆种在破瓦罐里的月季花和江西腊花;屋檐下的青石板旁,用碎石搭建的狗窝里,一直陪伴着女主人的老黄狗短短几天老了很多,失魂落魄的屋里屋外到处转悠着、不时低声哀叫着……
今天我们见到的却是破败不堪的断壁残垣,大半个房顶尚在,顶上的烂麦草早被风揪扯得七零八落,勉强残存的也变成腐殖土被饽饽丁覆盖占领了;黒木门洞开着,烂掉了的柜门再也看不出曾经的朱红色亮漆,谁也不敢进屋去,老墙在风中颤颤巍巍,似乎随时都会坍塌,找不到一个壁虎的后代,就连它们也是向往着有人烟的庄户人家;院子里枯萎的驴尾巴蒿草比人都高一头,堂屋西边的破石缸它肯定不晓得自己曾经被公公向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念叨很多次。曾经的曾经的场景:日寇侵华的时候,公公跟叔公公还是顽童,鬼子来的那天,石缸里装满了大人蒸好了的枣饽饽,豆饽饽,豆腐粉条白菜陷的发面包子。鬼子见鸡杀鸡,见狗追狗,临走时还往饽饽缸里撒尿,大人孩子都缩在一起瑟瑟发抖,不敢吱声,刚刚赶回家的公公小哥俩最好的朋友大黑狗火了,猛地蹿上去狠狠地咬了撒尿的鬼子兵一口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溜烟的跑远了,鬼子兵的鬼哭狼嚎端的是让小哥俩解气得荡气回肠,公公的每一次复述也都让我们做小辈的展颜欢笑,暗呼快哉。当年的英雄大黑狗更是我们永远的追忆。
当年奶奶用来对小哥俩施行家法的鸡毛掸子上的曾经五彩斑斓的鸡毛已经烂得看不出模样了,它曾经很多次光临过公公的梦里,婆婆说似乎每一次公公都会咯咯咯地笑醒了,然后孩子般把酣睡中的老妻唤醒,跟她讲述他当年做顽童时气得母亲一蹦三丈高时的斑斑劣迹,他返老还童般欢快的复述中更多的是对作古的母亲的怀念:他的母亲是一个贞烈的寡居女子,两个幼子是她唯一的依靠,她不敢有半点儿闪失。可是顽童又哪里能明白家长的担心,七岁八岁狗都不待见的年纪,村子是库区,离米山水库很近很近,弯一根针,绑在棉槐条子上就是一根鱼竿,哪管大人的千叮万嘱,夕阳不落山是不会回家的,大人的千呼万唤是统统听不见的,直到掌灯时分,拎着三五串鲜活的鱼凯旋的将军般大摇大摆的进门,随后在高举着鸡毛掸子的小脚母亲的哭骂数落中挣脱出来抱头鼠窜,回忆中母亲不再有一丝丝严厉,就连被母亲高高举起的鸡毛掸子也充斥着久违的久远的温馨。
祖宅的断璧残垣,公公跟叔公公久远的昨天,就这样逐渐湮没在岁月中,那些曾经的炊烟袅袅只能在梦里重温……(文/云在山间)
三十五年前,老宅还算齐整,远不像此际这般破败不堪,那时公公去世没几天的母亲是一个很要好很洁净的老婆婆,她的住屋可是井井有条。尽管房顶是麦草苫的,炕及灶台是泥巴抹的,房间也很狭小,但满是残留的温馨的烟火味儿。那时见证着曾经的盎然生机的三个大燕窝还完好的挂在屋檐下。外墙上肥肥的壁虎急急爬行的样子有几分滑稽,墙缝里的壁虎蛋很多;墙顶上的几株狗尾巴草哦满潇洒地在风中摇摆,不断的弯腰挑衅婆婆种在破瓦罐里的月季花和江西腊花;屋檐下的青石板旁,用碎石搭建的狗窝里,一直陪伴着女主人的老黄狗短短几天老了很多,失魂落魄的屋里屋外到处转悠着、不时低声哀叫着……
今天我们见到的却是破败不堪的断壁残垣,大半个房顶尚在,顶上的烂麦草早被风揪扯得七零八落,勉强残存的也变成腐殖土被饽饽丁覆盖占领了;黒木门洞开着,烂掉了的柜门再也看不出曾经的朱红色亮漆,谁也不敢进屋去,老墙在风中颤颤巍巍,似乎随时都会坍塌,找不到一个壁虎的后代,就连它们也是向往着有人烟的庄户人家;院子里枯萎的驴尾巴蒿草比人都高一头,堂屋西边的破石缸它肯定不晓得自己曾经被公公向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念叨很多次。曾经的曾经的场景:日寇侵华的时候,公公跟叔公公还是顽童,鬼子来的那天,石缸里装满了大人蒸好了的枣饽饽,豆饽饽,豆腐粉条白菜陷的发面包子。鬼子见鸡杀鸡,见狗追狗,临走时还往饽饽缸里撒尿,大人孩子都缩在一起瑟瑟发抖,不敢吱声,刚刚赶回家的公公小哥俩最好的朋友大黑狗火了,猛地蹿上去狠狠地咬了撒尿的鬼子兵一口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溜烟的跑远了,鬼子兵的鬼哭狼嚎端的是让小哥俩解气得荡气回肠,公公的每一次复述也都让我们做小辈的展颜欢笑,暗呼快哉。当年的英雄大黑狗更是我们永远的追忆。
当年奶奶用来对小哥俩施行家法的鸡毛掸子上的曾经五彩斑斓的鸡毛已经烂得看不出模样了,它曾经很多次光临过公公的梦里,婆婆说似乎每一次公公都会咯咯咯地笑醒了,然后孩子般把酣睡中的老妻唤醒,跟她讲述他当年做顽童时气得母亲一蹦三丈高时的斑斑劣迹,他返老还童般欢快的复述中更多的是对作古的母亲的怀念:他的母亲是一个贞烈的寡居女子,两个幼子是她唯一的依靠,她不敢有半点儿闪失。可是顽童又哪里能明白家长的担心,七岁八岁狗都不待见的年纪,村子是库区,离米山水库很近很近,弯一根针,绑在棉槐条子上就是一根鱼竿,哪管大人的千叮万嘱,夕阳不落山是不会回家的,大人的千呼万唤是统统听不见的,直到掌灯时分,拎着三五串鲜活的鱼凯旋的将军般大摇大摆的进门,随后在高举着鸡毛掸子的小脚母亲的哭骂数落中挣脱出来抱头鼠窜,回忆中母亲不再有一丝丝严厉,就连被母亲高高举起的鸡毛掸子也充斥着久违的久远的温馨。
祖宅的断璧残垣,公公跟叔公公久远的昨天,就这样逐渐湮没在岁月中,那些曾经的炊烟袅袅只能在梦里重温……(文/云在山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