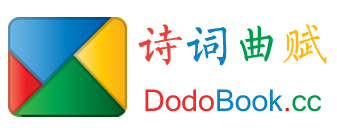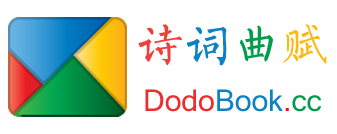你从未走远
- 精选散文
- 1076
- 21
- 2015-04-18
峰哥走了一年多了,但我常常感觉他并未走远。平时,总感觉峰哥有可能正在谁家聊天,也有可能在外地打工。有一天,他就会兴冲冲的迈进我家的门,喊一句:“大娘,我回来了。”
峰哥,你离去的时候,正是阳光明媚的春天。
我和几位亲友走在去你家的路上。村里哀乐低回,不知为谁嘶哑哭泣。仿佛有你从身后赶过来说:“走,快点,别让人家等咱。”走进你的家,院子里到处有人。有的蹲在墙角吸烟,有人从屋里不断地出来进去。正屋门口搭起了灵棚,南屋里支起了大灶,炊烟袅袅。各个屋的房檐下,都能见你做木工用的东西:锯、刨子、锯好的小方木……这些,你再也用不着了。
山顶上,人们哭泣着,围成一圈,把骨灰盒放进墓坑。姐姐把一本《封神演义》放在了骨灰盒边,她说,这是你最喜欢的书。山顶上填了一座新坟。新坟的四周是枯黄见绿的杂草。春风吹来,枯黄的茎叶瑟瑟作响。从山顶向下望,麦田已是绿油油的,呈现出勃勃生机。山脚下,有耕牛在犁地。本来,在这个年代,耕牛是派不上用场的。可在山坡上就不同了。每到春天,山谷间就会响起“喔-咿-驾”的吆喝牲口的声音。山腰上,还有两三个人在弯腰劳动。
一切尽如去年。
记得小时候一年的春天,我和弟弟跟着你在山坡上干活。地边上有几棵酸枣树,树枝间挂着几颗通红通红的酸枣。休息时,你要摘了给我们吃。酸枣树枝枝杈杈很多,上面满是刺儿。你伸出手,小心翼翼的把一粒粒的枣子摘下来。不过,即使你再小心,也难以避免被酸枣刺刺破了手。但你仍然高兴地举起手中的枣儿,高喊着:“睡吃,谁吃?”我和弟弟跳着,伸出手,喊着:“给我,给我!”你把手举得高高的,我们再跳也只能够到你的胳膊肘。你用两个手指夹住一颗枣,张大嘴巴,把手连同枣儿都放进嘴里--“吃了,吃了”,你喊着。而后,你会把酸枣一颗一颗的放到我们俩的手中,一人几颗,刚好平均,谁也没意见。黄昏时分,我们踏上回家的路。你推小车,我和弟弟坐在小车上。有时,你会突然喊一声:“坐稳了,小心!”我们就会大喊着,抓紧了车子。而你,故意使车子压上一块石头,再猛地一掀车把,车子猛地一颠簸,你哈哈大笑。车上,你摘来的野花扎成一束,捆在车前,在风中招摇。
你是一个乐观、热心的人。我妈常常夸奖你说:“看看你哥,成天乐呵呵的,谁家有活,一叫就到。”你也经常说:“愁啥?愁也没有,和掉了八吊钱一样有啥用?人就得想开点。”我姐家里穷,盖房子没包工,找人盖。但是,人不好找,现在这个社会,都清楚,小工在外干一天,少说也得五六十元,谁在乎吃那顿饭。可你,至始至终靠在那里,一干就是半个月。为这个活,还耽搁了你外出打工。我姐过意不去,干完活后,给你买去了一箱酒,你当天就送了回去,说:“自己的事,再花钱,让外人笑话。”可我知道,为这事,嫂子和你吵了架。峰哥,街坊邻居都说,你是这一片里少有的好人。
如果有天堂,你来到那里,一定会找到我们的亲人。我的父亲-你大爷,我们的爷爷、奶奶,还有邻居夏三叔。他们看见你一定会吃惊,咦,你怎么来了?你一定会笑着对他们说:“马克思叫咱来,谁敢不来?以后有什么活,给我说就行了。”天上的亲人们,因为有了你,生活会变得更加有滋有味。你是从没有忧愁的,可在你走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却不止一次的做过类似的梦境:深夜,满天的乌云,大雨滂沱,无边的原野,空空荡荡,你从远处走来,嚎啕大哭:“娘,小东,你们在哪里?”回答你的只有风雨声,你在村子周围游荡,找不到家的方向。而你家,正大门紧闭。或许,知道你也很挂念家,我才有这样的梦吧。
我常常想,在这个世界上,你匆匆走过,应该没有太大的遗憾。在熟悉的土地上,耕作过,唱过,收获过;在家里,付出过,爱过。你的儿子,虽然只有十三岁,可他却一直是所在中学的尖子生。你走后,去年六月,他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重点高中,这可是我们这一家子的光荣呀。
峰哥,在这个多少有点忘情的世界里,我牢记着你热心的面容。在茫茫的尘世间,不变的你,提着勤劳淳朴的灯笼,将善意热心化尽尘缘中。
你从未走远,也不会走远。(文/水星星)
峰哥,你离去的时候,正是阳光明媚的春天。
我和几位亲友走在去你家的路上。村里哀乐低回,不知为谁嘶哑哭泣。仿佛有你从身后赶过来说:“走,快点,别让人家等咱。”走进你的家,院子里到处有人。有的蹲在墙角吸烟,有人从屋里不断地出来进去。正屋门口搭起了灵棚,南屋里支起了大灶,炊烟袅袅。各个屋的房檐下,都能见你做木工用的东西:锯、刨子、锯好的小方木……这些,你再也用不着了。
山顶上,人们哭泣着,围成一圈,把骨灰盒放进墓坑。姐姐把一本《封神演义》放在了骨灰盒边,她说,这是你最喜欢的书。山顶上填了一座新坟。新坟的四周是枯黄见绿的杂草。春风吹来,枯黄的茎叶瑟瑟作响。从山顶向下望,麦田已是绿油油的,呈现出勃勃生机。山脚下,有耕牛在犁地。本来,在这个年代,耕牛是派不上用场的。可在山坡上就不同了。每到春天,山谷间就会响起“喔-咿-驾”的吆喝牲口的声音。山腰上,还有两三个人在弯腰劳动。
一切尽如去年。
记得小时候一年的春天,我和弟弟跟着你在山坡上干活。地边上有几棵酸枣树,树枝间挂着几颗通红通红的酸枣。休息时,你要摘了给我们吃。酸枣树枝枝杈杈很多,上面满是刺儿。你伸出手,小心翼翼的把一粒粒的枣子摘下来。不过,即使你再小心,也难以避免被酸枣刺刺破了手。但你仍然高兴地举起手中的枣儿,高喊着:“睡吃,谁吃?”我和弟弟跳着,伸出手,喊着:“给我,给我!”你把手举得高高的,我们再跳也只能够到你的胳膊肘。你用两个手指夹住一颗枣,张大嘴巴,把手连同枣儿都放进嘴里--“吃了,吃了”,你喊着。而后,你会把酸枣一颗一颗的放到我们俩的手中,一人几颗,刚好平均,谁也没意见。黄昏时分,我们踏上回家的路。你推小车,我和弟弟坐在小车上。有时,你会突然喊一声:“坐稳了,小心!”我们就会大喊着,抓紧了车子。而你,故意使车子压上一块石头,再猛地一掀车把,车子猛地一颠簸,你哈哈大笑。车上,你摘来的野花扎成一束,捆在车前,在风中招摇。
你是一个乐观、热心的人。我妈常常夸奖你说:“看看你哥,成天乐呵呵的,谁家有活,一叫就到。”你也经常说:“愁啥?愁也没有,和掉了八吊钱一样有啥用?人就得想开点。”我姐家里穷,盖房子没包工,找人盖。但是,人不好找,现在这个社会,都清楚,小工在外干一天,少说也得五六十元,谁在乎吃那顿饭。可你,至始至终靠在那里,一干就是半个月。为这个活,还耽搁了你外出打工。我姐过意不去,干完活后,给你买去了一箱酒,你当天就送了回去,说:“自己的事,再花钱,让外人笑话。”可我知道,为这事,嫂子和你吵了架。峰哥,街坊邻居都说,你是这一片里少有的好人。
如果有天堂,你来到那里,一定会找到我们的亲人。我的父亲-你大爷,我们的爷爷、奶奶,还有邻居夏三叔。他们看见你一定会吃惊,咦,你怎么来了?你一定会笑着对他们说:“马克思叫咱来,谁敢不来?以后有什么活,给我说就行了。”天上的亲人们,因为有了你,生活会变得更加有滋有味。你是从没有忧愁的,可在你走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却不止一次的做过类似的梦境:深夜,满天的乌云,大雨滂沱,无边的原野,空空荡荡,你从远处走来,嚎啕大哭:“娘,小东,你们在哪里?”回答你的只有风雨声,你在村子周围游荡,找不到家的方向。而你家,正大门紧闭。或许,知道你也很挂念家,我才有这样的梦吧。
我常常想,在这个世界上,你匆匆走过,应该没有太大的遗憾。在熟悉的土地上,耕作过,唱过,收获过;在家里,付出过,爱过。你的儿子,虽然只有十三岁,可他却一直是所在中学的尖子生。你走后,去年六月,他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重点高中,这可是我们这一家子的光荣呀。
峰哥,在这个多少有点忘情的世界里,我牢记着你热心的面容。在茫茫的尘世间,不变的你,提着勤劳淳朴的灯笼,将善意热心化尽尘缘中。
你从未走远,也不会走远。(文/水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