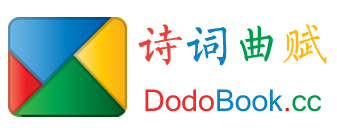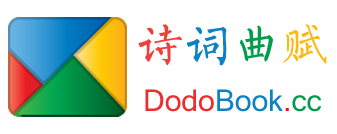姻缘
- 岁月静好
- 1173
- 7
- 2015-04-18
提起我和陶玲玲的姻缘,还得从岳父说起;说起岳父和我的传奇,还得从一件小事说起。那件小事,发生在我非常熟悉但是今天已面目全非的巷子里。
那天,我在住过的巷子里徘徊着,竭力寻找它原先的风物,哪怕是一点残存的蛛丝马迹。一排排高楼,闪烁着现代气息里千篇一律的玻璃窗,既没有蛛丝,也没有马迹。我寻找留恋的气息,寻找的晕头转向,彻底失望了。甚至产生怀疑,它真的是我度过漫长少年时代的小巷吗。我累了渴了,站在幼小的行道树下,垂头丧气,不知所以。
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巧在这时后,看到了那个钱夹子。一个赭色的钱夹子,静静地躺在行道树旁,躺在洁净的仿大理石的地面。
我捡起了钱夹子,没有东张西望寻找失主,也没有去藏匿,抑或偷偷地拿到某个角落看它的内容。我是当场打开的,拉开了拉链,却喜从天降。不瞒你说,我不知怎么形容当时我的高兴劲儿、张狂样儿。如果你在场,一定会以为我神经失常,或者是个白痴。钱夹子首位,放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不是别人,就是我朝思暮想正在寻找的陶玲玲。陶玲玲她,脸还是那么圆圆的红红的,眼还是那双葡萄似洋溢光彩的,鼻子端庄,嘴巴含笑,尽显令我陶醉欲仙的妩媚。
突然,我知道钱夹子的主人是谁了。
我不累也不渴了,恨不能洗个澡理下发,换上一套时髦的衣裳,站在这儿等他——等那位钱夹子的主人。
过了一会,他果然来了。他头发白多了,脸上的皱纹密多了,还带着那副老掉牙的玳瑁边眼镜,埋头东瞧西瞅地走来了。我没有举起,也没有藏匿,赭色的钱夹子,就那么拿着,静静地绞手在原地站着,镇定的眼神里,忍不住露出一丝得意。
果然,他走上前来了。像往常失主发现拾物者那样,惊讶、询问、交谈,接过了钱夹子,打开来了,仔细看了。却不清点里面的钱钞,也不对我表示谢意,那怕是一个表示感谢的表情。反而透过眼镜片逼视着我质问:
照片呢?
什么照片?我像一个演员,不知所以地反问他。
我钱夹子里,有一张照片的。
我控制着心中的得意,无语。
我女儿的照片呢?他又问了一句,逼视我,自言自语道,我想念女儿,想念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女儿问起我的近况,我就对她倾吐了心中的思念,懂事的女儿迅即拍了一张近照,邮来了,怎么就没有了呢?
我暗自紧咬牙关,没露出丁点破绽。
他按了按内衣的衣兜,掏遍了外衣内外所有的衣兜,气急败坏地说: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放在钱夹子里的呀!
我把演技发挥到了极致,反而温和地奉劝他:你最好再仔细想想,也许放在别的地方了。
没,没有,没有放到其他地方,我是放在钱夹子里的。
我无语,坚持无语到底。
我和陶玲玲,是在这条巷子里长大的。那时巷子窄狭,留下了我们多少脚印啊!说不完道不尽的细节,证明我们是地地道道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渐渐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虽然一天天近在咫尺、耳鬓斯磨,说老实话,心里像小鹿跳撞,却没有半句谈情说爱的言语。后来,折磨的不行了,我在城外对着东流的河水,大声演练了无数遍:玲玲,你知道吗,我爱你!可是,没有表达的机会。他母亲去世早,父女两一块生活,学校里不行,我家里也不行,适宜表达爱意的环境,就是她的家。从小你来我往的,我们经常去她家的小院里玩,院里的邻居都熟悉,大家对我们熟视无睹,好像面对两只叽叽喳喳的麻雀。我两也曾在她院里或家里,在她家客房或她的小住屋里说这说那,可有了表达爱意心思,却没有机会了——玲玲的父亲好像看出了什么,丝毫不给我两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他就像一个贴身的保镖,不,简直像玲玲的影子,玲玲走到哪里,他就斯根到哪里,丝毫不放松警惕。我父亲虽然也是一名公务员,却是最低层——办事处的,年轻时上面老干部挡着,中年了没有年青人的青春朝气,他不改弦易辙,依然认真于普通而繁琐的事物;母亲在幼儿园当老师,辛苦地干到了副园长,反而失去了教师的高雅,沦落为一位勤杂工似的在园里忙这忙那;弟弟过早地南下打工,妹妹仍在读书。尽管我们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但我明白从事企业技术工作的玲玲父亲那份心高气盛。心里的情感荡漾着,天长日久,就像深埋的老酒,越来越芳香醇厚了。芳香醇厚却没有机会一起陶醉。陶玲玲她爸非但不给机会,反而用一种逼视的眼神,促使我改变了在她家表白的想法。后来,我就集中精力准备高考,再后来,我就去北京读书了——走的那次,陶玲玲送我,他也送我——在月台上一直陪着玲玲,直到我们不懈地摇手再见。
却没有再见。哎,一言难尽!
我大学毕业回来了,陶玲玲已去北京打工了。三年离别,我们太年轻,也太老实了,只在心里默默地记着对方。你看现在,昔日的小巷已面目全非了,多年的邻居街坊也都鸟雀散,也不知她家搬到哪去了。看来要找到陶玲玲,非得下大功夫不可了。玲玲,虽然上了大学,我爱你的那颗心,一直没有改变;需要改变的,是你对我的误会。我怎么会是那种人呢,怎么会上了大学就见异思迁,忘掉心爱的人呢。正当我旧地重游,设法想方寻找线索,打算找到陶玲玲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却有了和陶伯伯的巧遇,而且重要的是,他全然认不出我了。意识到冥冥之中,上天不愿看到人间,又出现一部新时代的梁祝悲剧。
陶伯伯虽然带着遗憾离开了,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第二天,我们果然又在昨天那个地方,相遇了。闪着眼镜片后面恳切的眼光,他又追问我:
你真的没拿走照片?
我说:真的没看见照片。
他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好像故意说给我听:这就奇了怪了,一千多元现钞原样子没动,偏偏把那张照片丢了。
我心里等待着什么,却什么也没等到。陶伯伯悻悻地走了,我也没精打采地走了。我跟踪他,跟踪了一段路,他却停下脚步,不走了。我跟踪失败,却充满了信心,情知一定会找到她家的新址,打听到玲玲的电话的。
还是在变了样的巷口,炎夏的阳光格外灿烂,我甚至在行道树上看到了麻雀,我和陶伯伯又见面了。这一次他主动迎了上来,镜片后的眼神洋溢着微笑,站在我面前高兴地说:你拾金不昧的事,我给玲玲在电话里说了,女儿说现在像你这样拾金不昧的人少了,他很快就要回来了,回来一定当面感谢你。
听了这话,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我们闲聊起来,我就得知了陶玲玲的许多事:她至今仍珍藏着一幅画,一副初中同学送给她的一副国画,画上是两株清秀的青竹,写满了生机勃勃的人字,题名为:“让我们携手在百尺竿头”,高考落了榜,头两年她觉得无颜见人,和同学们都断绝了来往,后来出外打工,毅然不听劝阻去了北京,竟然在中关村站稳了脚跟。她又有一年多没有回家了,马上却要回来当面感谢拾金不昧的人。
听着他的话,我心里像吃了蜜,细细品味蜜糖般的滋味,我品味出一个问号:回想几天来在原先的小巷口,我和陶伯伯的巧遇,仔细琢磨前前后后的细节,我断定我们邂逅相遇的第一眼,陶伯伯就认出了我。他分明是在考察我,考察我的一颗心。我幸运的过了关,他又在牵红线。可我心灵深处弄不明白,从拒绝破坏,到主动牵红线,他是怎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是良心发现,是玲玲逼迫,还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见了玲玲,就有了答案。
我和玲玲的重逢,重逢后来往的喜悦,就不必细述了,像往常那样,热恋中的男女都有类似的体验。总之天格外的蓝,天上翩飞的白鸽特别的炫目,一切的一切都十分美好。已回到家乡和我一起在电脑制作行业创业的玲玲,也没找到答案。
结果,还是在得知他患晚期肝癌后猜测的。陶伯伯检查出病情,一直对女儿隐瞒着。我们发现他隐瞒的病情,也不再细述了,那样要增添很长的篇幅。总之,我和玲玲得知属于他的生命不多了。爱情的甜蜜、创业的艰苦、加之对亲人的留恋、对病魔的无奈,交织在一起,都要对待和担当。我们相信爱情的力量,坚决在复杂境遇担当一切。
已经不大关心的答案,还是时有透漏——陶伯伯不止一次感叹自己的自私。我们理解。从小要带玲玲,他一直没有再婚。他对女儿心怀深厚的父爱,他怕失去她,担心她嫁错郎;他对我及我们家太熟悉了,这种熟悉在他看来,是太普通太平凡了,距离期望中女儿应有的幸福,也相差太大距离太遥远了。这种意识,迫使他长久的横亘在我们中间,直到发觉属于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才有了根本的改变。我和玲玲理解他,把善待他生命最后的历程放在了首位。这样的善待也有弊端,不知何时正确处理婚事,是在陶伯伯弥留之际,用婚礼给他精神上带来安慰呢,还是以后?在弥留之际,会触及他心灵的伤疤。将我画的那副:“让我们携手在百尺竿头”贴上墙,在矛盾中虽然我们同居了,仍不顾一切给他治疗与照顾,因为毕竟是他的转变,才促成了我们的幸福。
我和玲玲做爱时,想起一句俗语:儿女自有儿女福,我的头脑里,甚至闪现一个恶毒的想法:从根本上说,是肝癌成全了我们的姻缘。恶毒一闪现,我就坚决地过河拆桥——义无反顾地痛击病魔。只有击溃交织着爱与恨的病魔,婚礼才如愿以偿,获得盛大和圆满。
那天,我在住过的巷子里徘徊着,竭力寻找它原先的风物,哪怕是一点残存的蛛丝马迹。一排排高楼,闪烁着现代气息里千篇一律的玻璃窗,既没有蛛丝,也没有马迹。我寻找留恋的气息,寻找的晕头转向,彻底失望了。甚至产生怀疑,它真的是我度过漫长少年时代的小巷吗。我累了渴了,站在幼小的行道树下,垂头丧气,不知所以。
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巧在这时后,看到了那个钱夹子。一个赭色的钱夹子,静静地躺在行道树旁,躺在洁净的仿大理石的地面。
我捡起了钱夹子,没有东张西望寻找失主,也没有去藏匿,抑或偷偷地拿到某个角落看它的内容。我是当场打开的,拉开了拉链,却喜从天降。不瞒你说,我不知怎么形容当时我的高兴劲儿、张狂样儿。如果你在场,一定会以为我神经失常,或者是个白痴。钱夹子首位,放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不是别人,就是我朝思暮想正在寻找的陶玲玲。陶玲玲她,脸还是那么圆圆的红红的,眼还是那双葡萄似洋溢光彩的,鼻子端庄,嘴巴含笑,尽显令我陶醉欲仙的妩媚。
突然,我知道钱夹子的主人是谁了。
我不累也不渴了,恨不能洗个澡理下发,换上一套时髦的衣裳,站在这儿等他——等那位钱夹子的主人。
过了一会,他果然来了。他头发白多了,脸上的皱纹密多了,还带着那副老掉牙的玳瑁边眼镜,埋头东瞧西瞅地走来了。我没有举起,也没有藏匿,赭色的钱夹子,就那么拿着,静静地绞手在原地站着,镇定的眼神里,忍不住露出一丝得意。
果然,他走上前来了。像往常失主发现拾物者那样,惊讶、询问、交谈,接过了钱夹子,打开来了,仔细看了。却不清点里面的钱钞,也不对我表示谢意,那怕是一个表示感谢的表情。反而透过眼镜片逼视着我质问:
照片呢?
什么照片?我像一个演员,不知所以地反问他。
我钱夹子里,有一张照片的。
我控制着心中的得意,无语。
我女儿的照片呢?他又问了一句,逼视我,自言自语道,我想念女儿,想念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女儿问起我的近况,我就对她倾吐了心中的思念,懂事的女儿迅即拍了一张近照,邮来了,怎么就没有了呢?
我暗自紧咬牙关,没露出丁点破绽。
他按了按内衣的衣兜,掏遍了外衣内外所有的衣兜,气急败坏地说: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放在钱夹子里的呀!
我把演技发挥到了极致,反而温和地奉劝他:你最好再仔细想想,也许放在别的地方了。
没,没有,没有放到其他地方,我是放在钱夹子里的。
我无语,坚持无语到底。
我和陶玲玲,是在这条巷子里长大的。那时巷子窄狭,留下了我们多少脚印啊!说不完道不尽的细节,证明我们是地地道道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渐渐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虽然一天天近在咫尺、耳鬓斯磨,说老实话,心里像小鹿跳撞,却没有半句谈情说爱的言语。后来,折磨的不行了,我在城外对着东流的河水,大声演练了无数遍:玲玲,你知道吗,我爱你!可是,没有表达的机会。他母亲去世早,父女两一块生活,学校里不行,我家里也不行,适宜表达爱意的环境,就是她的家。从小你来我往的,我们经常去她家的小院里玩,院里的邻居都熟悉,大家对我们熟视无睹,好像面对两只叽叽喳喳的麻雀。我两也曾在她院里或家里,在她家客房或她的小住屋里说这说那,可有了表达爱意心思,却没有机会了——玲玲的父亲好像看出了什么,丝毫不给我两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他就像一个贴身的保镖,不,简直像玲玲的影子,玲玲走到哪里,他就斯根到哪里,丝毫不放松警惕。我父亲虽然也是一名公务员,却是最低层——办事处的,年轻时上面老干部挡着,中年了没有年青人的青春朝气,他不改弦易辙,依然认真于普通而繁琐的事物;母亲在幼儿园当老师,辛苦地干到了副园长,反而失去了教师的高雅,沦落为一位勤杂工似的在园里忙这忙那;弟弟过早地南下打工,妹妹仍在读书。尽管我们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但我明白从事企业技术工作的玲玲父亲那份心高气盛。心里的情感荡漾着,天长日久,就像深埋的老酒,越来越芳香醇厚了。芳香醇厚却没有机会一起陶醉。陶玲玲她爸非但不给机会,反而用一种逼视的眼神,促使我改变了在她家表白的想法。后来,我就集中精力准备高考,再后来,我就去北京读书了——走的那次,陶玲玲送我,他也送我——在月台上一直陪着玲玲,直到我们不懈地摇手再见。
却没有再见。哎,一言难尽!
我大学毕业回来了,陶玲玲已去北京打工了。三年离别,我们太年轻,也太老实了,只在心里默默地记着对方。你看现在,昔日的小巷已面目全非了,多年的邻居街坊也都鸟雀散,也不知她家搬到哪去了。看来要找到陶玲玲,非得下大功夫不可了。玲玲,虽然上了大学,我爱你的那颗心,一直没有改变;需要改变的,是你对我的误会。我怎么会是那种人呢,怎么会上了大学就见异思迁,忘掉心爱的人呢。正当我旧地重游,设法想方寻找线索,打算找到陶玲玲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却有了和陶伯伯的巧遇,而且重要的是,他全然认不出我了。意识到冥冥之中,上天不愿看到人间,又出现一部新时代的梁祝悲剧。
陶伯伯虽然带着遗憾离开了,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第二天,我们果然又在昨天那个地方,相遇了。闪着眼镜片后面恳切的眼光,他又追问我:
你真的没拿走照片?
我说:真的没看见照片。
他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好像故意说给我听:这就奇了怪了,一千多元现钞原样子没动,偏偏把那张照片丢了。
我心里等待着什么,却什么也没等到。陶伯伯悻悻地走了,我也没精打采地走了。我跟踪他,跟踪了一段路,他却停下脚步,不走了。我跟踪失败,却充满了信心,情知一定会找到她家的新址,打听到玲玲的电话的。
还是在变了样的巷口,炎夏的阳光格外灿烂,我甚至在行道树上看到了麻雀,我和陶伯伯又见面了。这一次他主动迎了上来,镜片后的眼神洋溢着微笑,站在我面前高兴地说:你拾金不昧的事,我给玲玲在电话里说了,女儿说现在像你这样拾金不昧的人少了,他很快就要回来了,回来一定当面感谢你。
听了这话,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我们闲聊起来,我就得知了陶玲玲的许多事:她至今仍珍藏着一幅画,一副初中同学送给她的一副国画,画上是两株清秀的青竹,写满了生机勃勃的人字,题名为:“让我们携手在百尺竿头”,高考落了榜,头两年她觉得无颜见人,和同学们都断绝了来往,后来出外打工,毅然不听劝阻去了北京,竟然在中关村站稳了脚跟。她又有一年多没有回家了,马上却要回来当面感谢拾金不昧的人。
听着他的话,我心里像吃了蜜,细细品味蜜糖般的滋味,我品味出一个问号:回想几天来在原先的小巷口,我和陶伯伯的巧遇,仔细琢磨前前后后的细节,我断定我们邂逅相遇的第一眼,陶伯伯就认出了我。他分明是在考察我,考察我的一颗心。我幸运的过了关,他又在牵红线。可我心灵深处弄不明白,从拒绝破坏,到主动牵红线,他是怎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是良心发现,是玲玲逼迫,还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见了玲玲,就有了答案。
我和玲玲的重逢,重逢后来往的喜悦,就不必细述了,像往常那样,热恋中的男女都有类似的体验。总之天格外的蓝,天上翩飞的白鸽特别的炫目,一切的一切都十分美好。已回到家乡和我一起在电脑制作行业创业的玲玲,也没找到答案。
结果,还是在得知他患晚期肝癌后猜测的。陶伯伯检查出病情,一直对女儿隐瞒着。我们发现他隐瞒的病情,也不再细述了,那样要增添很长的篇幅。总之,我和玲玲得知属于他的生命不多了。爱情的甜蜜、创业的艰苦、加之对亲人的留恋、对病魔的无奈,交织在一起,都要对待和担当。我们相信爱情的力量,坚决在复杂境遇担当一切。
已经不大关心的答案,还是时有透漏——陶伯伯不止一次感叹自己的自私。我们理解。从小要带玲玲,他一直没有再婚。他对女儿心怀深厚的父爱,他怕失去她,担心她嫁错郎;他对我及我们家太熟悉了,这种熟悉在他看来,是太普通太平凡了,距离期望中女儿应有的幸福,也相差太大距离太遥远了。这种意识,迫使他长久的横亘在我们中间,直到发觉属于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才有了根本的改变。我和玲玲理解他,把善待他生命最后的历程放在了首位。这样的善待也有弊端,不知何时正确处理婚事,是在陶伯伯弥留之际,用婚礼给他精神上带来安慰呢,还是以后?在弥留之际,会触及他心灵的伤疤。将我画的那副:“让我们携手在百尺竿头”贴上墙,在矛盾中虽然我们同居了,仍不顾一切给他治疗与照顾,因为毕竟是他的转变,才促成了我们的幸福。
我和玲玲做爱时,想起一句俗语:儿女自有儿女福,我的头脑里,甚至闪现一个恶毒的想法:从根本上说,是肝癌成全了我们的姻缘。恶毒一闪现,我就坚决地过河拆桥——义无反顾地痛击病魔。只有击溃交织着爱与恨的病魔,婚礼才如愿以偿,获得盛大和圆满。